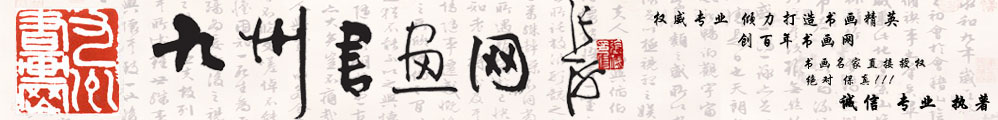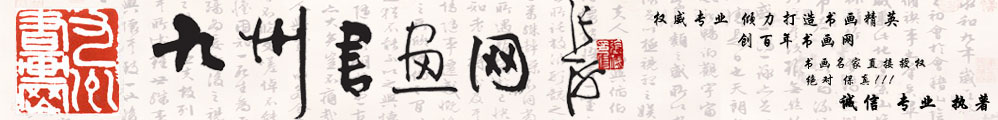改朝换代
民国三十八年(1949)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。在一个暮春的早晨,肉铺里的王倌匆匆赶到下塘吴家,对范氏说:“太师母,今天叫小龙不要去上学了。街上都是败兵,听说新四军打来了。街上都在装店板。”
“达达达达”……塘河里有火轮船开过,吴士龙胆子很大,来到前门的一个被子弹打穿的洞孔中窥望:见从东面开过来的一只火轮船上有许多穿黑制服的兵,轮船后面拖着一条大船,船上的兵都是穿黄军装的,两船上的兵好像要开始火拼了。因为火轮船上的兵想把绳缆解下,不想拖着后面的大船。“砰!”穿黄军装的兵朝天开了一枪。吴士龙马上被祖母拖到了里屋。
没几天,有步兵、骑兵从街道上经过,由东面乌镇炉头方向沿着运河过来,这支队伍一刻不停地过了一天,傍晚在南皋桥外的野草地上休息,准备过夜。好多人去看,吴士龙也跟着去看。见他们在唱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人们在说,这些兵不叫新四军,叫解放军。
石门镇解放了。
土改开始了,吴家的省吃俭用积下的七八十亩土地,改得只剩下九亩六分。由于没有放租,土地的耕作是由三个长工与农忙时雇用短工来经营,故此,在评成份时给了吴家一个“工商兼地主”,所以房屋没有改掉。那时,吴家已有两套大住宅,另一套是吴南山的弟弟吴鹤山之子吴保康硬要卖给吴顺发的。在解放前夕,吴保康对吴顺发说:“我要去台湾了,这套房子五百银元,你不要也得要。”结果保康拿了五百银元,死于那次有名的黄浦江沉船事故中。传说此次沉船是中雷,其实非也,那次去台湾之人群,大多带足金条银元及珠宝,而是超重在风浪中沉没。
学武之梦
一九五0年是解放后的第一年,社会逐渐平稳。在小镇上,除了常有马戏团来演出,还有越剧、木偶戏、小热昏等等,在茶馆里,还常常有地方说唱的三跳,称之为唱欠书。所谓欠书,一般有二种,一是欠了别人一大笔钱,到期无法归还,那就得拿出一笔钱来请三跳艺人说一部“书”,大约说上三四天,作为歉意答谢,让地方上人都去听;一是指偷了人家东西,被人抓到,尽管东西归还,但还得拿出一笔钱来请三跳艺人说一部书,表示歉意与知耻,也是为做贼的人消除业障。
吴士龙那年十岁,最喜欢听说书,尤其喜欢听那些武林高手,如何拜师,如何苦练功夫。当时他听了一部叫《金台传》的,金台的师傅在昆仑山,武艺高深,首先叫金台练指力:以拇指和中指,在蚊帐顶下的弧形布面上用力地抓撮,要在每天早晨没有小便之前抓撮一千下,睡前也是一千下,天天不间断,等你抓到了布,功夫就算到家。吴士龙即日起就在自己的蚊帐下抓撮,抓了一个多月,抓得手指都发酸了,还是没有抓到。
方莲珍问吴士龙:“你要练它做啥用呢?”
吴士龙说:“我要练成一身功夫,去闯天下,打抱不平。”
“你不当画家了?”
“画家也要当,武功也要练,当大丈夫就要文武双全。”
方莲珍觉得这孩子有点傻,说道:“打抱不平是要吃苦头的!”
“我不怕。”吴士龙说着又跑到园子里去练功了。这回他用左手拎动一只酒甏,在酒甏里,已积有一小半石子,他今天又放进一粒石子,据说一天放进一粒石子,如果积满,将有一百多斤,估计要花好几年才能积满。此事给达章阿叔见到了,他说:“小龙啊,你练功不能瞎练!没有师傅指点,是要练出毛病来的!”
吴士龙一听,觉得有道理,便暗自琢磨,生出一念:必须去昆仑山拜师。
这年吴士龙上四年级,在班级里已有点小名气了,学校的墙报报头画,都是他画的,成绩又好,所以他胸前挂起了红领巾,可是他的顽皮性,也在不断地扩张。每当下课的铃声一响,他便冲到操场一角约有四米高的古坟丘上摆擂台,凡是冲上去的人基本上都被他摔下去。这天,一个六年级里的大同学,他见了不顺眼,便大摇大摆地走上去,想把吴士龙摔下去,当他刚上去,用手指指下面说:“识相点,给我爬下去,不然,我一脚扫你下去。”吴士龙直觉来者不善,但要是爬着下去,那可丢脸!他急中生智,往教室处一看,说道:“许老师(教导主任)来了!”那大同学回过头去,吴士龙即一个下蹬,猛抱那人的一只腿,用力往向下冲,两人一起滚到了下面。那大同学觉得没有面子,便想挽挽袖子打人,下面的好多同学大家一起喊:“大欺小,脸不要;大欺小,老来吮八刁……”那大同学觉得不好意思,便红着脸走开了,离开时指着吴士龙说:“你小心,我下趟收作你!”这句话,其他同学听了倒无所谓,但吴士龙听后便很是心颤,毕竟这个大同学要大好几岁呐!那时的学校不像后来,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。
“我必须拜师学武艺。”吴士龙自言自语地说,便与同桌张世绅,背后桌子的钟洪毅说:“我已决定去昆仑山学武功,最好我们三人同去。”张世绅说:“啥时候动身?”
等过两天就清明了,我们就在清明日上路,带点粽子、甜麦塌饼,我新年里的拜年钿,压岁钿,还没有动过。你们有么?”
“有。”
“都带上。”
“万一用光了呢?”
“不要紧。”吴士龙蛮有把握地说:“我把《芥子园画传》带上,到时候我画几幅画,你们去卖,不是有钱了么?”
“好。”钟洪毅大一岁,他很不在乎地说:“船到桥门自会直。”
他们约好在清明日那天早上,在南皋桥上集中,不见不散,并要在枕头底下压一告别信,大意是:
爸爸妈妈:
我要去昆仑山学武艺,学成回家,可以打平天下无敌手,可以孝敬你们。大约三五年回来。
不孝孩儿启上
这些语句大多是听说书学着的。
清明夜(即清明节前晚上)家家户户在吃螺蛳,吃好后要把螺蛳壳撒在屋上,据说这样,房屋上就不会生瓦毛虫的。照往年,这事由达章叔去做,但今年,母亲要小龙去撒,说他已长大了,须练练臂力。吴士龙当然高兴,抓起螺蛳壳,使劲向屋上撒,撒得很有力也很高,达章叔在一旁称赞,吴士龙对达章叔说:“这点算不了什么,我前天在河边削水片,嚓嚓嚓嚓一直可以削到对岸。”
晚上,当大人们还在下面聊天时,吴士龙一人先上楼了,他对母亲说:“姆妈,我班级里明日要去远足,我要拿点粽子与甜麦塌饼。”方莲珍当然同意,说:“粽子在吊篮里,甜麦塌饼在橱里,你自己拿好了。”
吴士龙在楼上找到了一只小藤篮,把《芥子园画传》用一块蓝印拷花小方袱一包,放在藤篮底上,把国语书、常识书、算术书放在上面,当他把算术书放下去时,在手上停留了一下,他想算术书不要带去,又不喜欢算术,祖母常说算是算不好的,常言道:算得骨零圆,剩个箍罗圈,所以他把算术课本放进书包里,把一只小砚子,几枝乌龙水毛笔,一支金不换墨,用一张牛皮纸包一下,塞在《芥子园画传》旁边。就这样,把小藤篮藏在房门背后,就上床睡觉了。吴士龙睡得很香,连他母亲什么时候睡进来都不知道。吴士龙每夜都要做梦,这晚又飘飘然地进入了梦乡:他穿起一双小元宝套鞋,是父亲从肉店对面的孙双庆广货店里替他买来的,踩在水坑里,没有浸水,兴奋地冲到河边,双脚收不住一直往河里冲,却轻松地冲到了河对岸,他来回了几次都很成功,许多同学都看到了,说小龙真有本事,他说这是轻功,是昆仑山上的师傅教我的。一同学说:“你什么时候去过昆仑山?”
“哎!是昨天。”
“昆仑山好远好远,”一同学笑起来说:“除非你能飞。”
“哎,师傅是教了我飞。”
“那你飞飞看。”
“好。”说罢,自己把手往前一伸,胸脯一挺,果然离地了!只要把胸脯一挺,头一昂,就往上升,把手一平伸,就往前飞去了,同学们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,觉得还是再飞往昆仑山,自己的本领还没学到门。虽然能在天上飞,水面上踩水而过,但是还不能遁地,不能穿墙过壁,倘若我去打抱不平,被坏人关起门来,我就飞不出去,便得吃亏。像《金台传》中的土行孙,可以遁地而逃,可以穿墙脱身。他飞呀飞呀,忽然眼前一片漆黑,觉得头上有一只大手在摸他,这只手冰凉冰凉,他记得师父的手不是这样的,这一惊,他醒来了。原来是母亲的手在摸他的头,吴士龙忽地坐起来,正好床前写字台上的时鸣钟响了五下,他定了定神,梦中的事还记忆犹新。他悄悄地下了床,穿好衣服,把房门背后的小藤篮拎了,轻手轻脚地下得楼梯,在吊篮里提了两串粽子,放在昨天就准备好的杭州小提篮里,开开橱门,一摸甜麦塌饼,甜腻腻的沾手,不好带,便抓了一个吃着。这时天渐渐亮开了,听见达章叔与老长工章家佗伯在说话:“橱房间里有野猫。”吴士龙即刻提了两只篮直奔大门,轻轻拔下门闩,出得门,又把门拉上,便直奔南皋桥。
到得桥上,见张世绅和钟洪毅早已到了,他们都说:“昨夜没睡好,早已到桥上等你了。”吴士龙说:“好,快走,我父亲快要到店里去,路过桥上,见了我就说不清了。”
他们一直往南走,走过了南观音堂,又过了太公渡,福严渡,吴士龙总算透了口气,但还得继续快走,不能停,因为太公渡里面的李家石桥,有他的亲戚姑丈爹爹,若被撞见,就说不清了。出街上市的乡下人很多,他们都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三个小街佬人……
过了小羔羊渡,又到了六里亭,他们知道离崇德县城还有六里路,便在亭子里歇一下,各自拿出粽子来吃。一边吃,一边谈开了,钟洪毅说:“可以走到长安镇上火车到上海,到了上海,我们再坐江轮一直往西。”因为他同父亲去过上海,到外滩看江轮,说可以乘船到汉口、重庆,离昆仑山就近了。张世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很旧很旧的地图,一张解放前的全国地图,是从他爸的书柜里见到的。他说:“昆仑山不远,只要一直往西北去就是了。”吴士龙说:“那我们得去杭州方向,杭州在西面,上海在东面,不能朝反向走。”钟洪毅说:“你不懂,听我不会错。”他们走着争论着。张世绅说:“我听吴士龙的。”钟洪毅没有话说了。
不觉前面到了三里桥,三里桥好像比南皋桥要高一点,他们三人便跑上桥顶观望崇德县城。此时尚未近午,城中炊烟缭绕,塘河边柳荫桃花,燕子在桥下掠水而过,河中摇过一只小船,坐着一家人,是上坟后回归城里。吴士龙忽然想起了他没有到老太公与爹爹的坟上去上坟,有点内疚,再一想,不要紧,待学得武功归来再上坟,那更好。正在想着时,忽然面前站着一个大人。“哎!你不是顺发儿子小龙龙么?”吴士龙抬头一看,原来是与父亲一起做过蚕种生意的张东森伯伯。他一想,“完了!”忙叫了声:“哎,东森姆伯。”吴士龙见他穿一件很干净的兰布长衫,头发梳得很亮,鼻子下留着一排胡子,睁大了眼睛看他,很严肃。“你到这里来干啥?”张东森又见到边上还有两个孩,都带着包裹藤篮,惊问:“你们要做啥?到哪里去?”
“我们要去昆仑山学武功。”还是小龙开了口,“东森姆伯,你回去不要多讲,我们学好武功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“嘿嘿!你们知道昆仑山在那里?知道昆仑山离这里有多远?”
“在西北方向,我们看过地图,不远。”
“放屁!我告诉你们,到昆仑山有十万八千里路,就算你们每日走三十里路。你们算一算,三六十八,一个单程要6000日,就算你们不吃不用,来回至少要四十年,四十年!你今年几岁?”
“十岁。”
“嘿!到那时已五十岁了。可能你们的父母早已气死了……快给我回去!”
吴士龙三个瞠目结舌,一动不动。张东森觉得说得太重了,便用软语道:“小龙啊,乖,快跟伯伯回去,我是到三里桥来等候快班船的。”说时从南面过来一只绍兴乌蓬船,有三支橹在摇,速度很快,张东森即招手,要他们在桥下停靠,说有四个人上船去石门。他们赶紧到桥下桥盘石上等候。一到船上,快班船的老板娘即叫起来:“喔唷,顺发家儿子。”吴士龙也认得这家快班船是下塘南皋桥堍一户姓孙的绍兴人开的,他们每天从石门到长安要打两个来回。
吴士龙见东森姆伯与老板娘在互递香烟聊天,张世绅与钟洪毅两人,靠在一包货上睡着了,但吴士龙却心潮起伏,想想要学武艺真难,为啥从前人这么方便呢?
“你在想啥?”张东森见吴士龙皱起眉头若有所思,便笑嘻嘻地问道。
“我在想,我们这里为啥没有会武功的人。”
“有咯。”老板娘用绍兴话说。看来张东森已跟她说了孩子们的行动。吴士龙便惊喜地问:“在哪里?”
“就在芝村,有个伤科郎中,武艺高强,拳头打得蛮好。”张、钟二人也醒来了。“好了,你不要空出念三,老早死脱了!”张东森把眼睛向老板娘瞪了一下说,“如果那老郎中还活着,你们爸爸妈妈也不会让你们去的。你们还是安心读书吧。将来考大学,干一番大事业,才有出息。”说着说着,南皋桥越来越近,吴士龙对张、钟二人说:“你们看,这是吴士龙的美丽故乡。”三个都笑起来。是的,在水上远望,石门镇小巧玲珑,南皋桥在静静的水面上与倒影连成一起,像一只方楞厚重的雕刻精美的指环。当渐渐临近时,这座桥又显得雄拔而伟岸,透过桥洞左边,一排临水而筑的阁楼房舍是那么的错落有致,又有小划船轻快而悠然淌过河面,皱起阵阵漪涟。一只大船,刚刚过了高桥便竖起桅杆,只见两个男子,“沙拉、沙拉”地升起了白帆,他们一蹬一蹬地拉着,鼓起了双臂的肌肉,嘴里哼着:“嗯、嗨呀、嗯、嗨呀”,那节奏,那架势,振开了饱满的帆羽,那船头下也渐渐地展开了汩汩跳跃的波涛。再看那两个拉帆的小伙子,他们没有坐下来休息,一个拿着篙子,一个拎着绳球,守在船头上。因为在顺风快速的航行中,容易发生意外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!
吴士龙他们上岸后,见张东森给了老板娘一些钱,并对吴士龙说:“让他们各自回家。我要同到你家里。”
到了家里,正好吴士龙祖母不在,方莲珍在绣花,见儿子回来,并有张东森跟着,便道:“小龙,你说去福严寺远足,要很晚才回来,做啥介早就回来呢?”
吴士龙不出声。张东森如此这般地与莲珍说了一番,最后说:“好了,也是上祖有力,正好碰到了我,回来就好,不要说他了。”
“他说谎。”方莲珍瞪着眼睛,照儿子脸上狠狠地拍了一记耳光说:“你这细犟才,从小看大,你以后还说谎么?”
吴士龙眼泪直淌下来,但没有哭出声来。方莲珍从来没有这么重打过儿子,也心疼,一下子把儿子抱在怀里,吴士龙才开始哭了,说:“姆妈,我错了。”张东森见母子相抱而哭,心里也很感动,说:“好了,莲珍,我相信小龙是乖孩子,他会去掉野心好好读书的。我家里还有事,我去了。”
这时一只小黑狗奔了进来,在吴士龙身边摇头晃尾,这狗是他家养的,名叫黑狸,常陪在祖母身边,吴士龙知道祖母要回来了,赶紧擦干眼泪。
吴士龙回到学校,还是调皮捣蛋,自称是拉拉国主席,他用竹木等材料,自制了许多刀枪一类的武器,并在玻璃瓶中放入石灰,充当手榴弹,在星期天与甲班同学开战。结果对方的一个同学头上流血受伤,便哭着跑到吴家。吴士龙祖母即刻拿出用甲鱼血拌石灰制成的止血药为其包扎,吴士龙母亲马上去石灰甏里拿了一包酥糖给他,并说:“是我家小龙不好,你乖,别哭。”
这件事被学校知道了。吴士龙被记了一“过”,他的红领巾被除下,还开除了他的少年儿童队队籍。
农民万万年
一九五一年是抗美援朝最紧张的一年,学校的墙报上每天要出宣传画。吴士龙会画画的才能被派上用场。
到了第二年上半年开学时,吴士龙由于画宣传画得到好评,又把他的红领巾戴上,恢复了队藉。
一九五三年夏,吴士龙因算术不及格,没考取初中而痛哭。有一种失落感,就在家临摹《芥子园画传》,并复习算术,准备来年再考。
一九五四年,吴士龙再考初中,其算术总算及格,但他家成分不好,而且他的成绩报告单上品德的评定是丙下,所以又不被录取。因为当时学校少,考生多,要好里挑好。
“三五反运动”开始了,吴顺发每日落市后要去税务所交代,把偷税漏税的情况报出来。如果你报得少,报得不足,就要去镇北市梢的新桥西堍的后郑车榨油坊内“望台湾”。望台湾当然是跪在台上望,叫你哭笑不得。
因为吴顺发胆小,怕跪,就按照税务所的要求,同意把税交足。他回家把在后郑车见到的情况,讲给了母亲与妻子听了。他母亲范氏说:“看来,开店做生意是呒啥做头了。把山货行鱼行与肉店都关掉算了。”因为现金凑不起这浩大的所得税,只有把多年积下的金条抵上,还有为吴士龙定做的金锁金链条也凑上,他们认为这是在消灾。
那年,吴顺发三十六岁,觉得自己身体强健,做田畈算了。况且,历年来在农忙时,他又在田里做过双活,懂农活。土改剩下的九亩六分地,可以养家了。方莲珍当然不反对,母亲范氏常说衙门前,一蓬烟;生意年,一千年;农民年,万万年。就这样,“吴顺昌山货行”关门了。给了工友们一点钱,让其归家另谋生计,其店房租给了别人。
再说达章阿叔,此时他已回灵安老家。起先,他当了村长,入了党,后来当了大队书记。梅珍也出嫁了,嫁给石门近郊一户贫下中农。吴士龙祖母给了她好多嫁妆,像嫁女儿一样。要吴士龙改称她为拜娘,即干妈,因为梅珍属鸡。
与商无缘
一九五四年下半年,“三五反运动”结束了,做生意的又开始好起来。范氏又定了个主意,让儿子顺发做田畈,孙子士龙送到一家南货店学生意,吴家的店面房子还在,等三年学徒满了,照样可以开店做生意。这是范氏的如意算盘。
“万顺生南货店”坐落在石门镇的市中心寺弄口东端,老东家陆炳荣刚过世,留下母子二人,正需要一个学徒帮忙。因为这家店是“吴顺昌肉店”的贴隔壁,两家关系很好。吴士龙见了老板娘只称呼她“炳荣娘娘”,其小老板陆新初刚好二十岁,吴士龙叫他新初阿叔。他们母子也没有把吴士龙当成小工友,没有任意使唤,或者说重话,他们只是把一些零星钞票放在偏僻处,看吴士龙见到后拿不拿,要试试他的人品。吴士龙见后即把钱拿给了炳荣娘娘,说这钱是谁放在那里的。炳荣娘娘若有所思地说:“噢,大概是新初放的。”过了几天,又在另一处见到了钱,吴士龙又交了。过了好多天,出现了一大把钱,在一个橱脚边。这次吴士龙没有去拿,只是拉着炳荣娘娘去看,炳荣娘娘骂了新初阿叔一顿。此后就没有这种事了。
吴士龙天真烂漫,根本不晓得在试探他。他所关心的是,每晚走上小阁楼,打开《芥子园画传》,一直要画到很晚才睡,因为他讨厌做生意的伪手段。比如秤半斤糖,必须是秤平平的七两半,当时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,用草纸一包,秤起来正好半斤;如果是秤一斤咸肉,必须打在十五两半上,而且秤得很“仙”,可以讨顾客高兴。如果碰到一个拗刁货,他要看秤花,你不妨按着秤硾线,很利索地一捺,把秤硾线捺到一斤的秤花上。秤好后,用两根湿稻草一扎,秤起来就不止一斤了。
若遇到农忙时,生意很清淡。吴士龙站在店堂里,往往要打哈欠,其原因还是晚上画得很夜深,所以白天无精打彩。炳荣娘娘开始对吴士龙不满起来,告诉了他祖母,说道:“全芳嫂,看来你孙子不是做生意的料,赶不上他父亲顺发。这两日生意又清,他还不断地打哈欠,好像夜里睏得不醒。每天在店堂里打哈欠,生意都被他打完了。” 吴士龙祖母听了很难过,把孙子叫到后堂,说:“小龙啊,你给我争气一点,学好三年,我们自己开爿南货店。”
“娘娘(祖母),我不想做生意。”
“你倒底要做啥?”
“我喜欢画画。”
“画画有什么用,去卖给谁?”范氏真感到是恨铁不成钢,悻悻然离开了南货店,路过南市街的“大新布店”时,有人喊她:“太亲母,进来坐坐,你做啥眉头簇结。”范氏一看,原来是吴士龙的娘舅方耀祖。她就走了进去,把吴士龙的情况告诉了一番,没想到耀祖眼睛一亮,说道:“好啊,龙龙这孩子聪明,就让他画画吧。”
“画,去卖给啥人?”
“我有个伙计姚惠林,你也晓得,他现在不吃布饭了,在崇德开了一爿铅画店。生意很好,让小龙去学画铅照,不是顶好末。石门镇上还没有一家铅照店呐。”
经方耀祖一说,范氏心里一亮。“好!”范氏站起来说,“七倌,你给我写张便信。”范氏是当机立断的人,又回到“万顺生南货店”,与炳荣嫂交代了一番,把孙子带回家,儿子媳妇都同意。
第二天,方莲珍给儿子穿上一件新做好的列宁装,那时刚过正月半,天气尚寒,头上给他戴了个八角解放帽,又把儿子最喜欢的《芥子园画传》放在小藤篮里,把换替衣裳用一个新的蓝印花包袱打扎好,让儿子背着,把他送到对过的快班码头。一路上跟儿子说:“你到了崇德,可住在大姨家里,她家是在北大街132号,你可叫大姨陪你到姚先生店里。这包钱你放好,交给大姨买蹄子,拜师的规矩。”方莲珍走了一阵又说:“噢,对了,还有,你抽空还可以去看看慈伯。”
“慈伯是谁?”
“他是你外公的表弟,他叫王羹梅,画画,他比你外公要画得好。”
“真的?!”吴士龙心里乐滋滋的。
“听说他是崇德县中的校长。”
“我怎么称呼他呢?”
“我想想看,”莲珍心里排辈了一下,说,“他排行第五,跟你外公并辈,应该叫他五爹爹(桐乡人称呼祖父叫爹爹)。”
立志当画家
就这样,吴士龙告别了母亲,上了机船快班,来到了崇德县城。那是一九五五年初春,是他第三次来县城,前两次是考初中时来过。
吴士龙很快就找到了大姨家。大姨是吴士龙母亲的四姊,叫方世敏,姨夫费西畴一直在上海一家公司当财务,很少回家,她儿子鸿祺九岁,还在上小学。家中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公费春波,老人很慈祥,问吴士龙道:“龙倌,你贵庚多少?”
“今年十五岁。”
“有何贵干?”老人开始口吃起来,后来才知道他是崇德有名的“费疙嘴”。
“我是来学画照生意的。”吴士龙把娘舅的介绍信交给了大姨。大姨说:“姚惠林就在前面,很近。现在还不到十点钟,大姨先同你过去见面。”
出了门,没跑上几步,大姨说快到了。吴士龙抬头一看,见一靠街玻璃门窗上有“时代画室”四个大字,下面两边挂有几只画好头像的镜框,吴士龙能认出来的一张是梅兰芳西装胸像。进店门是右边的一扇单门,大姨在前面先进去,就说:“惠林,你看,这孩子你还认得?”
“喔!下塘龙龙么,长得这么高了。”
吴士龙笑嘻嘻地叫了声:“姚先生。”
方世敏立刻递上介绍信说:“是耀祖写的。”姚惠林一看就说:“好!我知道龙龙能画,很聪明。”他点着头说,“我用得着。就是晚上睡觉……我这里地方小。”
“睡在我家,这你放心好了,过来又近。”方世敏接着说,“明朝一早来拜师,今朝就让他定定心,我去理出一间小间让龙龙住。”
吴士龙就随着大姨回去。吃午饭时,他跟大姨说要去看王羹梅五爹爹,大姨说:“好,你快点吃,吃好我们马上去。五爹爹是校长,事情忙,怕他吃好饭,马上要回学校。”
王羹梅原是石门湾“王恒泰米行”的少东,又是原国民党崇德县县参议,他原有五百多亩租地,在一九四八年,即解放前夕,他早已把租契借据当着佃户一一烧毁,米行及栈房统统卖光,并且退了国民党党籍,带着他的小老婆及一子一女,来到崇德,租了他住在上海的姐姐蔡家的一幢小洋房住着。由于他古汉语很有修养,就在崇德县中谋求了一个语文教师。其小老婆弹得一手好钢琴,嗓音甜美,在中学求了个音乐教师。解放后,王羹梅既无土地又无房产,而且已退出了国民党党员。调查一下民意,他没有恶劣的行迹,故口碑又好,但他过去的名声与威望还是很大的,人民政府还是把他评为“开明地主”。王羹梅总算松了口气,但有着地主这顶帽子,还是心有余悸,拿出了一盒金条,捐给中学作建设经费,故此他,在崇德县中还是德高望重的。原来那位国民党员的中学校长,解放前夕已逃往香港,人民政府就任命王羹梅为县中校长。王羹梅兢兢业业地一心扑在学校里,努力把学校搞好来,把他有生之年的全部精力投入于教育事业。他不抽烟不喝酒,唯独爱好书画,历年来购买的几箱子名人字画就藏在这所小洋房里。他时而取出来欣赏一番,或者临摹一回。
当吴士龙随着大姨来到河东一幢小洋房前,正好有一个穿着夹旗袍、长波浪披肩、大眼睛、五十左右的中年妇人站在门口张望。方世敏遂即喊道:“五婶妈,慈伯回来了么?”
“喔,世敏,我正在候他呀。”那人一笑脸上就出现两个酒窝,“我今朝上午呒不课。”又指着吴士龙问:“你同着这位是……”
“八娣的儿子,龙龙。你看,这么大了。”吴士龙母亲排行第八,故称八娣。
“喔,莲珍的儿子,我好几年之前看到时,记得有一个小辫子。现在是个小伙子啦!”
“他要来看看五爹爹,”大姨又对吴士龙说,“快叫五娘娘。”吴士龙接着就叫了声五娘娘。
“好,进来,进来。”五娘娘又说,“想不到龙龙这么大了,我们这些人是应该老了。”
进得里面,见客堂间很宽畅,朝南壁上挂着一幅任伯年的《寒林牧归图》中堂,对联是行楷,吴士龙认得,上联为“蝉声驿路秋山里”,下联是“草色河桥落照中”。
吴士龙在看画,大姨跟五娘娘在谈家常,当然也谈了吴士龙的事。正说着,外面有脚步声响来。
“慈伯,你回来了。”
“哎,世敏。这位是啥、啥啥人?”王羹梅有点口吃。
“下塘莲珍的儿子。”五娘娘说。
“五爹爹。”吴士龙连忙上去称呼他。见他六十左右,中等身材,面目清秀,加上一副金丝边眼镜,很文气。
“噢,是龙龙,我晓得,这孩子从小就喜欢画画。”
“好,龙龙,”五娘娘说,“先让五爹爹吃饭。让伊吃好饭,你再来同五爹爹聊天。现在让大姨同你到后花园里看看,等会我来叫你们。”
吴士龙跟着大姨,穿过一段走廊,来到一个半亩大的小花园。方世敏轻轻对吴士龙说:“五爹爹有个怪脾气,若有人看着他吃,就吃勿进去。”
这花园里的花,虽然还没有开,但有一股清香味。方世敏说:“龙龙,你看,兰花开得好来,香得和顺来。”这是吴士龙第一次见到真的兰花,觉得此花果然不同凡响,怪不得《芥子园画传》里有这么多人去画它!在朝南墙根假山边有一棵牡丹,已结花苞。方世敏说:“这是墨牡丹,不多见。”
“是开黑花的吗?”吴士龙好奇地问。
“不,带点红,是深紫色的。”
方世敏点着一棵枝桠交错的尚未发叶的树,对吴士龙说:“这树开木笔花,很好看。不过它的仔有剧毒,你晓得就是。”
他们看着看着,大约半个小时后,五娘娘过来了:“龙龙,五爹爹吃好了,你过来。”
回到客厅,见王羹梅在隔壁书房里一只摇椅上慢慢摆动。“老头子胃不大好,饭后要摆动一番,帮助消化。”五娘娘又对吴士龙说,“下午五爹爹不去学校,他很喜欢你,要跟你讲些画图经头。我去学校打个招呼,先走了,下午有音乐课。”
“我也要走了,让龙龙定心听五爹爹讲。”方世敏又说,“龙龙,你五点钟之前一定回来。”
“不,让伊吃得夜饭走好啦。”五娘娘说。
“勿要,让伊回来吃吧,不能麻烦你们。”方世敏说。
她们走后,吴士龙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画稿,皆是《芥子园画传》上的山水、花鸟。这些画画在白报纸上,像八开那么大小,有五六张。王羹梅接过画,细细看了一遍说:“龙倌,你画得很像,但是笔力不够,以后,你得用宣纸来临摹。西寺前的范长裕纸课店里有得卖。你是照着康熙年间出版的王概本么?”
“是的。是外公给我妈的那套。”
“那套书我也有,但已经落后。因为是木刻本,笔致很僵硬,对初学的人来说,很难得着笔法。”王羹梅立起身来,在书架上拿下一叠书,他翻开书道,“龙倌你看,这是光绪年间出版的巢勋临本。”
“也是《芥子园画传》?”
“是啊,它是石印本,虽没有浓淡,但他的笔触还是很自然,不走样,初学者学起来不吃力。”
“它没有彩色。”
“是啊,那没有办法。待将来印刷术发达了,龙倌你可临摹一套有浓淡彩色的。”王羹梅笑了。
“我来吗?”吴士龙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来的,有,有啥勿来?”王羹梅说话结巴起来,他一字一顿地说,“相信,自己来,就—一—定—来。”
吴士龙把巢勋本小心地翻看了一会,说:“真的比我这套要好。”
“你喜欢么?”
“嗯,喜欢。”吴士龙笑着,心想难道五爹爹能送给我。
“龙倌,你喜欢,五爹爹就送给你了。”
“谢谢五爹爹。”吴士龙兴奋得脸都红了。
“龙倌,你要搭我立个志。这一生,你,你就是要当—当—一—个—画家。”王羹梅说到这里,停了一下,盯着吴士龙,看着他那双乌黑铮亮的眼睛。吴士龙扪着嘴,顿了一下头。
“我相信,你,能成功。”
王羹梅接着又说:“你家里,你外公画的画还在么?”
“在,我常常拿出来看。”
“是啊,常常看看是好的。不过你外公画的还不算最好。你要多看好东西。”说着王羹梅站起来,叫吴士龙一起上楼。
在楼上房中挂有一堂蒲作英的墨竹。
王羹梅说:“这画是清朝晚期一个嘉兴人叫蒲华的,人家叫他蒲邋遢。此人我见过,人虽有点邋遢,但画面却有一股清气,因为他有学问,故此,他画出的画,笔笔含蓄,刚柔相济。”
这时的王羹梅像变了个人,一点也不口吃,他又转向吴士龙说,“所以啊,你要多看书,多看文学书,读读唐诗宋词。我知道你算术不好,考不上中学,家里成分又不好。哎……不要紧!考不上中学就意味着没有机会进大学。不过大学毕业没花头,只不过是掌握了一套准确的自学方法,仍须不断努力钻研,才有成果,你没机会进大学,没关系,只要你比读大学的人多看书、多写字、多画画,同样你若掌握了一套准确方法,再加上不断努力钻研,你终归会出成果的,说不定会比读大学的人强,在他们之上。人要自强不息!世界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人。”
王羹梅呷了一口茶,又顿顿实实地对吴士龙说:“龙倌,你得看书,看书,只有多看书,才是上进之道。”这段话吴士龙到老不忘。
接着,王羹梅又从乌木箱里拿了出来几件画:任伯年的牡丹双鸡、吴昌硕的梅花、吴石仙的江城夕阳,最后他拿出两幅山水,用叉头挂了起来说:“龙倌你来看,这一幅是吴伯滔画的,这一幅是吴待秋画的。他们是父子俩,是崇德镇上人,都已故世。我喜欢其父亲吴伯滔的画,你看,笔头松溜溜,用墨又滋润,有书卷气。”
“啥叫书卷气。”吴士龙好问。
“哎,书卷气就是笔有尽而意无穷,用笔很清逸,不霸道。你看,这幅他画得不是很繁密,他松紧有致,有意境。不像他儿子吴待秋画的,虽繁茂而不空灵,一般以为丰实,里相东西多,所以缺乏书卷气。”五爹爹讲得顺顺溜溜,接着又说,“你晓得为啥?因为吴待秋不读诗词,只知道一天到晚地画。不像他父亲吴伯滔,看书、有学问。”吴士龙记在心中。
“五爹爹你画的画给我看看,听我娘讲,你画得比外公好。”王羹梅笑了,说:“画得并不好,但自己蛮得意。”说着,他从写字台抽斗里拿出一幅小品来:画的是两只粽子,其勾线清朴用色典雅。遂问吴士龙道:“龙倌,你看看,哪一只是肉粽子,哪一只是夹沙粽子。”
吴士龙一看,马上就指出来了。即说:“我看不是像不像粽子,五爹爹你画神了,比真的粽子有味道。”
“所—所—所以呀。”王羹梅又口吃起来,“画画要画得好,并不是靠临摹别人的画,而是要多观察真东西。”停了一会,王羹梅胀红了脸说,“当—当—当然,临摹也很重要。掌握技法,还是要靠临摹。你还得临帖,毛笔字写不好是不行的。”吴士龙句句听着,真使他豁然开朗,对五爹爹说:“我记牢,谢谢五爹爹。”
房间里的时鸣钟敲了五下。吴士龙忙说:“呀唷,已经五点钟了。五爹爹我要回去了,怕大姨等急。”“那好,我就不留你了。这套巢勋本你带去,得好好临摹。你等一下。”王羹梅又从书架上翻出一本柳公权字帖,遂说,“龙倌,这本帖送给你,可先用薄薄的连泗纸蒙在上面,用小毛笔勾出空心字,然后用中楷笔填满墨,这叫摹,临摹,临摹,得先摹后临,就事半功倍。这是古训。”王羹梅又把吴士龙送到门口,结结巴巴地说:“在姚惠林那边画擦笔铅画,是无所谓的事。不过学会了,可以混口饭吃。这种画,我也玩过,很简单,只要细心就是。”他回身指着内堂说,“你看,我父母亲的两张像,是我用擦笔炭粉画出来的。”
吴士龙高兴地回到费家,见大姨已等在门口,旁边一个小男孩奔来叫:“龙哥哥,你的床铺,姆妈同你搭好了。”这是吴士龙的表弟费鸿祺,也是好几年不见了,他们携着手,很是亲热。
吃好晚饭,吴士龙在电灯光下看画谱,他兴奋得无法入眠。那时,石门家中不比这里好,还没有装电灯。
第二天早上,吴士龙是被大姨叫醒的:“我已买好一只新鲜蹄子,快吃好早粥过去行拜师礼,快起来。”
到了“时代画室”,出来接蹄子的是一个烫短发、大眼睛、小圆蛋脸的女人,方世敏对吴士龙说:“这是师母。”吴士龙笑着叫了声,又在姚惠林面前跪着叫了声:“先生。”姚惠林立刻说:“喔唷,起来,起来,现在勿行这套啦。”又说,“今朝,让龙龙先在边上看我画,我会边画边讲。”大姨说了声:“龙龙你用心看,我就去了。”
吴士龙见旁边上还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师兄,在打九宫格,并用HB铅笔,在格上勾头像轮廓,他不时地在看放大镜下面的照片。再看姚先生,他也在看放大镜,并在勾好头像轮廓的铅画纸上擦炭粉,姚先生一边擦一边说:“要由淡到浓,一点点加浓,要耐心,不能急。”
上午,不时有人来催拿画像,还有拿照片来要画像的。
吃过午饭,吴士龙对姚先生说:“先生,下午我想画一张试试看,好吗?”“喔,不行,你师兄克明,他三年了,我还是不让他画。你只有半天,笑话。”克明师兄瞟了吴士龙一眼,露出轻蔑的一笑。由于这一笑,便把吴士龙激了起来,即说:“先生,我有把握画得像,你让我试试,倘使我画坏了,这张铅画纸,我赔钱。”姚惠林一想,不错,吴家有钱,就让他画吧。
“好吧,待我拣一张年纪大一点的,画起来容易像,年轻的,要画得像有难度,因面部特征少。”姚惠林找出一张乡下老太婆的照片,说:“好,就在窗口这张小桌上画吧。九宫格,放大镜,这里有一套用熟了的擦笔,你用吧。不懂就问。”
吴士龙把照片夹在九宫格玻璃上,一看是密密麻麻的几十行格子,他觉得不需要太多格,就粗略地打了五六行格子,很快地把轮廓勾好,就动笔擦起来。他很聪明,先找了一张废画纸试擦了一番,觉得顺当了,便直接画起来,一句也没有问。大约四点钟左右,他把残留的铅笔格子线用橡皮擦掉,就给姚先生过目。
“喔,像倒很像,但是,你在明暗过渡的地方,太硬,你得用棉花球轻轻擦一下,让伊和顺一点,看起来就舒服了。”姚先生露出了笑容,他拿出棉球,细细地修饰了一番,留着几个部位让吴士龙去完成。
结果到了五点多一点,一幅头像画成,姚先生把它用夹子夹在沿墙壁的铅丝上。
第二天上午一早,吴士龙刚到画室,只见一个中年男子进来,对挂在墙上的老太婆画像直叫:“喔!我娘画得像来!”接着对姚惠林说:“姚先生,多少钱?”
“三万元(合现在三百元)。”
“好,我给你。”
姚惠林自然很高兴,对吴士龙说:“我不要你快,你要画得仔细,你一天画一张就是了。”又对他的大弟子说:“克明,你一天必须勾两张格子稿。”
“先生,我画的照像还是我自己打格子。”吴士龙接着说,“我自打格自己有数。”
“啊!你这呆佗,我想让你轻松点!”
“不用不用,我喜欢自己弄。”
就这样,吴士龙每天画一张。方世敏过来看了也高兴。晚上在电灯光下临摹巢勋本《芥子园画传》,三天来,他已画了十多张,想拿去给五爹爹看,打算第二天吃过午饭过去。
想不到的是,次日上午九点钟左右,方世敏急匆匆过来说:“不好啦!慈伯捉进去了。”
吴士龙直跳起来:“不可能吧。”
“真的,茶馆里都在讲。我听着后就去他屋里,五婶妈在哭,说是人家诬告他,讲伊出卖共产党。”吴士龙马上站了起来,向姚先生请假,说:“我今朝一定要去看看五娘娘,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姚惠林说:“好,那我同你一块去,王羹梅做人不错,刚解放那年,我到石门你娘舅布店里寻个饭碗,也是王羹梅介绍过去的。”
他们来到蔡家洋房,五娘娘在发呆,书房里翻得一塌糊涂。她把大门关上,细细地讲述了一番。
王羹梅在石门湾的家产是数一数二的,他父亲曾三次被周边的土匪拔过财神。王恒泰老东家为了保身家,让儿子加入了国民党,由于他为人正直,并有才华,故他便列入了石门县党部参议员。那时日伪期间的维持会会长祁秋繁,是个五毒俱全的人,经常要向王羹梅借钱,其实是有去无回的。在解放前,祁秋繁又要向王羹梅借五十大洋,但王羹梅一个子儿也没有借给他。故此,祁秋繁怀恨在心。解放后,那些国民党人一个个地入狱,在狱中都传开了,王羹梅是开明地主,共产党很宽大他,并当上了县中校长,生活很优裕,与小老婆两人住在蔡家的花园洋房。所以祁秋繁一类人很是妒恨,只想寻找机会去弄倒他。
就在这段时间,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回老家石门湾,要调查一下她的胞妹共产党员张兰被害的原因。同时查问石门镇的两位地下党员陈丹墀、池菊荘的被捕原因,最好的线索是从监狱中提问那些石门镇伪职人员。当张琴秋提问祁秋繁时,祁一想机会来了,便道:“这事不好说,他现在红得要命,人民政府正重用他。”
“你大胆说好了,迫害革命先烈,不管任何人都得严办。”
“这事跟王羹梅有关,当时他有探子,官又大,他一句闲话,说了算。”
“你有何证据?”
“我官小,不知细底,你问他就清楚了。”
就这样,立即逮捕了王羹梅。
其实,这两件事都跟王羹梅不搭界。前者,张家也是有身价之家,与王家有往来,王羹梅绝不会去迫害她,最多劝导一下而已。后者,陈、池两位也是石门镇上富家之子,与王家又是世交。再说王恒泰是商界之列,唯有伙计职员,根本没有什么探子。还有一事可证实王羹梅无罪:解放前夕原来的县中校长是国民党党员,劝说王羹梅一起避居香港,王说:“我勿做亏心事,没必要走。我相信共产党会拎得清的。”这段情节是后来方世敏对吴士龙说的。五娘娘又说:“想想真后悔,到了香港就没事了……就是你五爹爹掉心不下这两箱子书画啊!”说罢泪流满面。
逮捕时,先用绳子把王羹梅扎扎实实一绑,老头子如逢晴天霹雳,一下子垮了,说话本来是口吃,结结巴巴得要命,一个通宵审讯下来,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王羹梅一直是养尊处优的,哪能经受得了这样的折腾。他不开口不吃东西,五娘娘买了一碗汤团送进去,他碰都不碰……
姚惠林安慰了五娘娘说:“事情总弄得清爽。你自己保重。”他便与吴士龙回转了。又隔了一天,上午十时许,方世敏又急匆奔进来说:“这下完了,布告贴了。慈伯判无期徒刑。现正在浒弄口茶馆门前宣判。”
吴士龙与姚惠林、大姨等人,急切切奔往浒弄口,一看人头挤挤,吴士龙一人钻到前面,见五爹爹双臂反绑着,头颈上吊着一块牌,写着“反革命分子王羹梅”,他没有戴眼镜,脸色灰青,人倾斜着,有一面一个背枪的兵携着他,站在用几块店板两条长凳铺起来的台上。吴士龙挤到了前面,见他两条腿在哆嗦着,吴士龙胆子很大,压低了声音叫了两声“五爹爹”,王羹梅渐渐睁开眼,见到吴士龙在叫他,眼泪直淌了下来,扭动了一下嘴巴:“五爹爹……冤枉。”声音很微弱,但被边上的一个兵听到了,喝叱道:“不许说话。”那时过来一个兵,把吴士龙拉到了边上。吴士龙此时看到边上还有三四个在台下站得规规矩矩的人,脚边还放着包裹,一会儿听到一个站在台子上的人宣读判处王羹梅无期徒刑,判处祁秋繁检举有功,当场释放。吴士龙这才看清了祁秋繁那家伙,个子不高,脸色黄白,扁而瘦。他背后的一个兵拉了他一把,说道:“你回去吧。”此人弯下身子背起包裹,挤了出去。立即有人指着他的背影唾了口水,骂道:“晦气东西,起泡货。”此人肯定听见,遂夹着身子,速速离去。
此后不到一月,王羹梅死于临平劳改农场,连尸体都没有领回。
当王羹梅死后三个月的一上午,快九点钟了,祁秋繁的阿哥祁三喜,没见其弟起床,便进房探问,祁秋繁即道:“阿哥,我要走了。”
“到哪里?”祁三喜惊讶地问。
“阎罗大王那边。”
“出空(讲梦话),你昨晚上不是好好的。”
“王羹梅来过了!”
“你又出空了,王羹梅拖牢洞死了。”
“不。他刚才还站在房门口催我。”
“看来我得去叫个医生。”说着,祁三喜往外去叫医生了。当他叫了西医冯熏陶,来到祁秋繁床前时,此人早已断气,并且双手双脚都交叉着,好像是被人捆扎了一样。冯熏陶观察了其瞳孔已散,即刻退出。
因石门镇不大,此事立刻传得家喻户晓,此为后话。顺便带上一句,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在文革时坠楼身亡,人们发现脚上只穿一只袜子,似乎不像是自杀。
再说我们的主人公吴士龙,由于五爹爹的突然死亡,他心情久久不能平复,晚上也没有好好临帖,夜里又睡不好觉,白天画铅照也没劲,一心想回家。当然回家有几种原因,一是,觉得这种画不深奥,就这点,会了。二是师兄作梗,因为妒嫉,常常使他找不到主要的擦笔,只有向先生要,先生有点怀疑他拿走。三是师母要喊他去洗菜,拎水。但先生不让他去,叫他自顾自画,师母就掼罗柱(什么都不干),往娘家跑,姚先生就跟她吵了起来。再说,吴士龙在自己家里,从来也没有碰过这种双活。所以他决定回家,以免给他家带来不愉快的争吵。
吴士龙这一走,他走掉了一个居民户口,他走进了二十年苦难的农民生活。然而却自觉地走进了一条通往绘画殿堂的阶梯。故此,他必须感谢他的师兄,感谢他的师母。 |